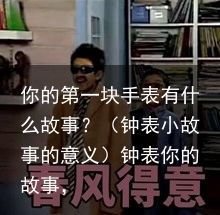金博男:秒针如何转动?从晚清科学小说看中国人对时间的全新认知(钟表小故事)故事钟表法,
摘要:“秒”最初为长度单位,经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时间改革,才开始成为一个时间单位。而拥有秒针的三针表于清朝中叶进入到中国以后,“秒”这个时间尺度才真正被用于计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把三针表只当做一种高级饰品来看待。因此,中国人关于“秒”的时间意识并没有因为三针表的流行而觉醒。之后,随着西方科学知识以及文化思想势不可挡地涌入晚清中国,“秒针”所象征的更加精确化的“时间”,终于开始像蒸汽机和“电气”一样,渐渐与科学及文明关联起来。而积极使用“时间”元素,完全由中国人创作的科学小说,也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便是先锋之作。在这篇小说中,徐念慈通过地底国与现实世界二者时间制度的设定与对比,完成了对诉说时间相对性这一中国文学经典母题的戏仿(parody),给当时的中国人带去了关于“秒”乃至“时间”本身的全新启示。
引言
明万历九年(1581)春,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由澳门再度来到广州。这一次他精心准备了一架自鸣钟,赠与当地一名叫黄应甲的武官。在这名武官的引荐下,罗明坚终于接触到了朝廷,他的传教活动也因此迎来了转机。[1]此架自鸣钟便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机械钟表。[2]时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罗明坚的继任者,明清时期最负盛名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南京街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会”,公开展示了包括自鸣钟在内的种种西方机械。由此,普通中国民众第一次得以领略机械钟表的风采。又三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将两架自鸣钟上的罗马数字换成十二地支,并镌刻上龙纹,献与当时的皇帝明神宗。[3]自此之后,西方的机械钟表及时间制度,便开始在中国普及开来。
针对近代中国的计时仪器与时间制度,迄今为止包括历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在西历、二十四小时制、星期制等时间制度受到海内外学者热议的同时,却鲜有人关注“秒”这个时间概念。目前,仅有学者湛晓白在其专著中讨论近代中国时间计量的精确化时,对“秒”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普及有所探讨。[4]而“秒”最初是如何被国人一步步认知,该认知又是如何变迁的?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两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什么是“秒”?“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这是1967年召开的第13届国际度量衡大会对于秒的定义。[5]除了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以外,包括笔者在内,普通人自然无法理解此段描述的具体含义。或许干脆将其当作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与科学仪器所得到的一个精密计算结果也不为过。而笔者想表达的观点是,阐释“秒”这个时间概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古代,“秒”最初并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长度单位。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孙子算经》[6]中,有如下记载:度之所起,起于忽。欲知其忽,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一秒,十秒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五十尺为一端;四十尺为一匹;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7]
十根蚕丝并排,其宽度即为“一秒”之长度。虽然《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度量衡的正式长度单位为“分、寸、尺、丈、引”,并不提“忽、秒、毫、厘”,好在《汉书·叙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以下说明:元元本本,数始于一,产气黄钟,造计秒忽。八音七始,五声六律,度量权衡,历算逌出。[8]
“造计秒忽”,意思即为计算要从“秒忽”开始。另外,关于“秒”的实际运用,我们还可以在《隋书》中看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圆周率数值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与“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之间。[9]时至唐代,度分秒计量体系开始形成,“秒”作为角度单位,被运用于天文学计算之中。例如,关于岁星(木星)出现后的移动轨迹,《旧唐书》里有如下描述:日行一百七十六分五十秒,日益迟一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九分。[10]
另一方面,关于时间的计量体系,古代中国最基本的时间制度之一是百刻制,顾名思义,一昼夜的时间被分成一百刻,“刻”便成为最基本的时间单位,配合漏刻使用。百刻制被认为起源于殷商,一直施行至明末。[11]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精确度在百刻以上的漏刻,例如北宋时期燕肃发明的“莲花漏”(图1),每一刻又可以细分成六十“分”。图1 南宋杨甲《六经图》卷三所录燕肃发明的莲花漏图解龙图燕公肃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尝做莲花漏献于阙下,后作藩青社,出守东颖,悉按其法而为之,其制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刻木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总六千分,以效日……[12]
一日“六千分”,“一分”即现代的14.4秒。除燕肃以外,元代人赵有钦发明的漏刻,其测量的精度甚至提升到了6秒。[13]但必须强调的是,明末以前的时间测量精度随着制造技艺的进步不断得到提升的同时,与之相匹配的时间单位却并不曾新增。而与中国情形完全不同的是,在14世纪的欧洲,虽然秒针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现代的“时分秒”计时体系早在1345年左右就已经出现。[14]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到的,这种计时体系16世纪末才终于通过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么,在没有现代精密科学仪器的明末,“秒”究竟是如何测量以及定义的呢?将自鸣钟带入中国的利玛窦对此有着堪称完美的回答。利玛窦来到中国,除了自鸣钟等机械以外,还带来了大量科学、天文学等西学著作,其中就有他的老师克里斯托佛·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u)的Astrorabium(《星盘》)。克拉维斯曾参与修订格力历即现在通行之公历,在数学、天文学等领域有着非凡的建树,可谓声名卓著。Astrorabium后来由利玛窦口述,经李之藻之手在1607年被译定为《浑盖通宪图说》,意即以图解的方式阐释天体运行。该书中便详细介绍了测定时刻所需的仪器以及具体的测量法(图2)。图2 定时尺分度图说(《浑盖通宪图说》卷下)图2中左下方的仪器称为“瞡筩”,是测量时不可或缺的工具。“瞡筩”中间有一“枢”——圆形小孔,在此“枢”上嵌入“分成式尺”,再通过对照天体角度与尺上数值,便可以判定时刻。[15]至于尺上的具体刻度,如图2中所示,从卯至午为90度,即30度为一时辰。至于具体度数与时刻长短的换算,书中专门制作了“度图”(图3)以供查阅。图3 度图(《浑盖通宪图说》卷下)度图中上方第一行的“度”,表示度数,而紧跟在“度”之后的“时”与“分”,实则表示时间,“时”即一小时,“分”即一分钟,与现代无异。该表最右一列,即1度到30度所对应的时间长度,分别为第二、三列所示数值,具体为1度等于“〇时四分”即4分钟,2度即8分钟,3度即12分钟……依此类推。中间与左边的“度”列同理,即31度至60度所对应的时间为2小时4分至4小时,70度至360度所对应的时间为4小时40分至24小时。[16]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方便计算与测量,利玛窦直接使用了西方的计时体系。至于中国的时刻制度为何不方便计算,利玛窦专门予以了说明:凡计日百刻者,每刻作六十分。每时有八刻又零二十分作二小刻,今节去余分以便镌记。故每日止九十六刻。[17]
如前文所述,直至明末,百刻制一直为中国的基本时间制度。而除了百刻制以外,广为人知的十二时辰制,早于汉代就已经出现。实际上,中国人长久以来是通过这两种制度互相配合来计时的。但是,如利玛窦所谈到的,将二者相换算的话,1时辰即8⅓刻,无论如何都会有余数出现。为了消除⅓刻这个余数,“小刻”的概念便被创造出来。将1刻60等分,其中10分即为1“小刻”,如此⅓刻即2小刻,1时辰即为8刻又2小刻。利玛窦觉察到上述换算殊为不便之后,便提倡索性将一日百刻改为九十六刻,那么1时辰即等于8刻。在如此改良的同时,利玛窦又导入了西方的“时分秒”计时体系,具体为:且以四刻为一时以便推算。每时共六十分,每刻得一十五分,而以一分为六十秒,一秒为六十忽。[18]至此,“秒”终于作为时间单位登场。现在,让我们回看刚才的“度图”(图3),表的最下方横排有三个标记:“分”“秒”“忽”。而需要注意的是,“度”列下方的“分秒”依旧是度数单位,只有“时”和“分”的竖列下方所表示的“分·秒”和“秒·忽”才为上述时间单位。也就是说,当“度”的单位变成“分”的时候,“时”列的时间单位也对应地变为“分”,而“分”列的单位则变为“秒”。按照刚才的方法,从上往下读,“〇度一分”所对应的时间为“〇分四秒”即4秒钟,“〇度二分”即8秒钟……最后的“三六〇分”即24分钟。而1度等于60分,360分即6度,根据表中数值6度所对应的时间为“〇时二四分”即24分钟,二者数值相吻合。同样,当度数的单位为“秒”时,时间单位相对应地变为“秒”和“忽”。所以,根据此表可以轻松得知,1秒钟即为0度0分15秒。在没有现代精密科学仪器的明末,“秒”究竟是如何测量以及定义的呢?用利玛窦所给出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太阳移动0度0分15秒角度所需要的时间,即为1秒钟。那么,让我们试着追问,作为角度单位的“秒”缘何会被当做时间单位来使用呢?在欧洲,“second”(秒)本就为角度与时间单位,所以导入西方计时体系之际,中国的角度单位“秒”也被沿用为时间单位,这自然不难推测。而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感受且计量时间的历史,本身就是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以及位置变化开始的。对于人类而言,角度,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确定的、可以让人信服的东西。所以,角度单位能够转化为时间单位,也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通过这种转化,进而使时间的暧昧性变得稀薄,成功地让时间成为一种可以被人类掌控且可以被描述的事物,这可以说是人类支配时间的历史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二、“三针洋表最时兴”康熙九年(1670),利玛窦所带来的“秒”被写入《清会典》之中,至此“秒”正式成为一个时间单位。[19]周日十二时,时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20]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秒”虽然正式成为时间单位,但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因为真正要测量一秒钟的时间,漏刻自不必说,即便使用上节所述利玛窦的计时方法,测量太阳0度0分15秒的位移也是万万不能做到的,即便勉强做到,也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而改变如此现状,使“秒”真正能够被测量、被捕捉到的,自然是拥有秒针的三针表的到来。关于三针表[21]的出现时间,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有以下考证:已知最早拥有秒针的弹簧驱动钟表——恐怕也是所有类型钟表中最早的——是弗雷莫斯多夫(Fremersdorf)藏品中,一个没有署名的“俄耳甫斯”钟表。其制作时间大约是1560年至1570年之间。[22]
自罗明坚16世纪晚期将机械钟表带入中国后,到18世纪中叶,不说民间,仅皇宫之内的钟表就已经多到数不胜数。传教士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曾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负责宫廷内机械钟表的管理和维修,据他所言,当时宫廷内仅出自巴黎及伦敦最顶尖钟表师之手的杰作,在18世纪30年代就已经超过了4000件。[23]至于三针表何时进入中国,很遗憾,确切的时间还无从得知。不过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我们确可以看到“铜镀金月球顶人打乐钟”“铜镀金转皮球花钟”等乾隆时期精美的三针表。同时,乾隆帝留下的许多关于自鸣钟的诗句,也可以作为佐证。例如,《咏自鸣钟》里如此写道: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水火非明藉,秒分暗自迁。[24]
在此还不得不提到徐朝后于1809年付梓的《自鸣钟表图说》。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机械钟表的内部构造以及维修方法的工具书,“反映了18世纪末以前中国的钟表技术水平”[25]。书中关于三针表有如下记载:一曰表。机轴如钟,收大为小,有单针、两针、三针、四针之别。单针指时指刻,两针并指分,三针并指秒,四针并指日。[26]
实际上,不仅限于皇宫内,即便是在民间,三针表也一度十分流行。[27]乾隆、嘉庆年间的诗人林苏门擅长作风俗诗,著有诗集《邗江三百吟》(1808)。其中收录一诗,题为《带三针表》,诗中写道:“二分明月要三针”[28],便是记录了扬州人追买三针表的情形。而比起诗句,我们更应该关注此诗的序文,关于三针表的构造以及当时社会背景,序文中有以下说明:此亦定时刻之物也。用铜胎瓷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藉法条为准。面上画如八卦,另嵌以针定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州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戴以为观饰。[29]
可见,三针表虽然在18世纪末以来受到民间追捧,但中国人所谋求的并不是更加精确的时间,归根结底三针表也不过是一件更加高级、昂贵的配饰或者玩具罢了。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仅发生在江南,北京亦是如此。例如诗人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1795)里,便如此吟诵道:三针洋表最时兴,手裹牛皮臂系鹰。[30]
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机械的态度,意大利历史学家契波拉(Carlo Maria Cipolla)曾有精彩的论断:当欧洲人使用透镜制造显微镜、望远镜和眼镜时,中国人则乐于把它当做令人着迷的玩具把玩。在对待钟表上,他们亦是如此。透镜、钟表和其他仪器为了满足欧洲社会文化环境的特定需求,才于欧洲出现,但在中国,这些发明属于从天而降的意外收获,所以中国人把这些东西当做奇技淫巧看待,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31]
至于秒针的发明,究竟是基于何种需求,又是如何“推动”欧洲社会前进的?换言之,欧洲的“秒针”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这对于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而言,恐怕是一个难以回答甚至难以想象的问题。因此,或许只有当中国人走向世界,亲眼目睹欧洲的“秒针”社会后,才能真正理解秒针的内涵之所在,知晓秒针的“正确玩法”。三、蒸汽、电气、秒针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1818—1891)受清廷之命前往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任驻外大臣。他在欧洲任职期间,深入欧洲社会,参观考察了众多工厂、学校以及政府机构。值得庆幸的是,他将这些所见所闻都事无巨细地写在了日记当中,让后人得以一窥究竟。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877年7月3日),这一天,郭嵩焘来到了英国“格林里叱”(格林威治)天文台。在天文台一层,他看到了数百件钟表陈列一堂,皆由海军专门送来进行试验:其试验有热度寒度之不同,以得热气流动则行加速,得寒气凝滞则行加迟,须是寒热如一,行乃有准。其热柜贮热水其下,上置钟表数十具,加盖其上。寒柜置冰亦然。其钟屋下有大时辰钟一座,置之地中,以四时气适均,寒暑无所加损。格林里叱所以取准时刻分杪者,必以此钟为定。[32]
西方钟表的制造技艺为什么能够日新月异?郭嵩焘在日记中如此分析道:水师钟表皆供国家之用,例应送验。钟表店制造诸器,不能送验也。徒以格林里叱时辰钟为伦教各处所取准则者,其试验尤精。每得一钟表最准者,由格林里叱定其等差,即声价为之顿增。是以皆乐得其一言以取重,而相与出奇争胜,技艺亦因以日进。[33]
可见,包括军事设备的开发与改良在内,西方钟表制造技艺的进步与其社会需求有着直接的关联,二者往往相互促进。除了钟表之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关于时间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玩味的记载。例如不管是“观星显远镜”还是测风仪,这些仪器的记录测量,在当时已皆可以精确到秒,而显然,郭嵩焘没有将这些细节忽略。因为提倡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郭嵩焘受到弹劾,于光绪五年(1879)受召回国。而同一年,另一个中国人又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旅,他便是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考察的徐建寅(1845—1901)。与郭嵩焘有所不同的是,徐建寅在其父亲徐寿(1818—1884)的影响下自幼学习“西学”,是大清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此次德国之行,也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赴国外考察的工程技术人员。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881年8月23日),徐建寅来到了德国“司旦丁伏尔铿”造船厂考察“雷艇”,在他的《欧游杂录》中,对当日情形有以下记载:同金翻译登雷艇试行,初次至半路汽机事件发热而停,未能试得确数,约一小时。至十一点半钟又行一海里,得三分二十六秒。回行一海里,得三分十一秒半。惟哈总办之表,则仅三分十秒半,当时已说明作十一秒计。后派郑清濂往试其数,由伊登记。[34]
从这段看似平淡的记叙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徐建寅而言,“秒”甚至已经无法满足他对船速的计量要求,而不得不使用“半秒”来记录,且对最后仅为“一秒”的测量误差,他甚至再次派人专门检验核实。徐建寅对时间的如此“斤斤计较”或许是基于一个技术专家的本能与自觉,但毫无疑问的是,比起国内竞相购买三针表的“趋时人”,他才是那个时代真正了解“秒针”之价值的人。当然,在当时不仅限于“雷艇”,包括火车、汽船等蒸汽动力机械的速度测量,甚至枪械、火炮等武器发射速率的测量,种种场合都务须精确到“秒”,而这些都会加快西方社会时间精确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西方“秒针”社会背后的另一只推手则是“电气”。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郭嵩焘的日记当中。光绪三年九月十日(1877年10月16日),郭嵩焘第一次亲眼看到并使用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于过去一年刚刚发明的电话。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如下写道:近年卑尔所制声报,亦用电气为之。上下楼由右引至左,相距约数十丈,安置电线,各设小木案以便凭坐。两端为木杵圆柄,纳电线其中,约长三寸许。上有圆盘,径二寸许,凡两层。内层缩小五寸许,上为圆孔,径八寸。衔马牙铁饼其中,薄仅如竹萌之半。上下并贴薄锡,中安铁柱,用电线环绕之。安置柄中,铁饼距铁柱中间不及一杪。据格里云:“人声送入盘中,则铁饼自动,声微则一杪动至二百,声愈重则动愈速,极之至一千,与耳中之膜纳声者同一机杵〔杼〕。声在耳中,如锥刺之,则自知痛,痛不在锥也。铁膜动,与耳中之膜遥相应,自然发声。”[35]
郭嵩焘虽然原原本本将同行外国人对电话工作原理的讲解记录了下来,但紧跟着又不得不发出“然其理吾终不能明也”[36]的感叹。关于“电气”,郭嵩焘在日记中还曾专门解释过电量的定义。量电之数曰发拉,曰迈古路发拉。每花〔发〕拉为一电池一秒钟过一息蒙阻力所发之电。[37]
“发拉”即电容的国际单位法拉,由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即原文中的“迈古路发拉”的名字命名。郭嵩焘对自己上述记录的具体含义很可能依旧一无所知,但这些陌生又抽象的名词与定义,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开始不断地进入到普通中国人的视野当中。1876年,也就是郭嵩焘来到英国的这一年,中国第一本自然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创刊。该刊旨在向中国人普及真正的西方基础科学知识,在当时收获以及培养了大批中国读者。包括“电气”在内的西方科学知识以及以“电气”为驱动的机械与器物,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清帝国之后,“秒”这个时间单位存在的真正意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察觉。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Wolfgang Schivelbusch)在其《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 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中谈到铁路的发明消灭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38]而不仅仅是以火车为代表的蒸汽动力机械,包括使用火药的枪炮以及使用“电气”的机器等等,同样都可以视为将传统空间与时间极度压缩之物。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发明他们的动机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换言之便是缩短时间。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之所以渐渐步入“秒针”社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机械由西方世界所发明,而更是因为这些机械的使用直接促使西方转化为一个更高效的社会。晚清人李圭的海外游记《环游地球新录》(1878)中记载的美国消防局的运行机制,或许是证明上述观点最为简单明了的一例:尤奇者,车房左壁有电机,旁有铜钟。何处起火,电信一至,钟亦藉电气自鸣,后槽系马绳亦因以自脱。马闻钟皆奔出,各就车前部位而立,五秒工夫可齐备出门。倘在夜间,则马奔地板声震甚,楼上火夫皆惊觉,衣裤靴帽悉于卧时整备,亦仅五秒时可穿齐。计自得电信至马车出门,日则五秒时,夜则十秒时耳。每分时车行一里。车上鸣钟,使行人避道,否则死伤勿论。[39]
通过这一系列生动详实的描述,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李圭个人也像徐建寅那样,“秒”的时间意识已经觉醒,但在他眼中所映射的追求高效的西方社会本身,对于19世纪70年代的大清帝国而言,还是一个尚且遥远的存在。然而,当西方最新的机器、科学甚至于文化与思想以不可阻挠之势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亦是如此,例如流行于明清时期的“猫眼定时”一说,在晚清之后便渐渐沦为批判的对象。[40]另外,星期制度的导入以及“星期日”的普及,也反映出了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巨大转变。[41]“秒”这个时间概念,或许与“星期”不同,在晚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曾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然而秒针所代表的不断精确化的时间本身,却逐渐与蒸汽机及电气并列,开始转化为科学与文明的象征,并带给中国人新的关于时间的启示。而晚清诞生的“科学小说”,又恰逢其时地为此种观念与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四、法螺先生的“时间旅行”晚清是小说的时代。在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这篇提倡小说创作、肯定小说价值的文论之后,一直被视为末流的小说,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科学小说”便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众多新类型小说之一。虽然以“科学”为名,但因为受到以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的影响,此类小说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浓重的科幻色彩。在晚清之前,像是《镜花缘》《荡寇志》等一批小说之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科幻的元素与描写片段,[42]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些小说中的科幻元素与“时间”并无关联,且“时间”也从不曾参与这些小说主体的构建。而另一方面,像是明末成书的《西游补》,虽涉及了“未来世界”的概念,但这个“未来”自始至终依旧存在于《西游记》的世界观以及时间框架之中。然而,当以凡尔纳为代表的西方科幻小说,尤其是那些让“时间”直接参与小说内容与主题构建的作品,于清末被接连不断地介绍到国内之后,不仅中国人的小说创作观念为之焕然一新,就连时间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构想了未来之中国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作为最初的尝试之作虽然没能彻底摆脱传统时间观念的束缚,[43]但从这篇小说开始,“把玩”时间要素,旨在将“时间”本身置于小说创作核心的作品,终于开始在中国出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的小说林社出版了一部“科学小说”,题为《新法螺先生谭》。作者署名“东海觉我”,即小说林社的编辑之一,晚清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徐念慈。时间回到1904年夏天,徐念慈的好友,同为晚清著名作家的包天笑完成了译作《法螺先生谭》。阅读此作后大受刺激的徐念慈,当即决定要塑造一个中国版的“法螺先生”。包天笑的这部《法螺先生谭》,转译自日本作家岩谷小波的《法螺先生——独逸の部》(1899)和《続法螺先生——独逸の部》(1900)[44],原作是由德国作家拉斯伯(Rudolf Erich Raspe)创作的《闵希豪森男爵叙述他在俄罗斯的奇妙旅行和战役》(1875),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徐念慈笔下的“新法螺先生”,其“奇妙旅行”大致经过如下:某日,新法螺先生登上一座足有三十六万尺之高的山巅。忽然,秒速达到数百万尺的大风自头顶吹来,最终导致他的肉体与灵魂分离。新法螺先生花了四十八个小时才搞清楚了所发生的一切,但通过种种实验,成功地发现了使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与分离的秘诀。分离出的灵魂还可以发光,所以他站在山巅,使灵魂大放光明以照亮全世界。他本想照醒在迷梦中沉睡的中国人,使其能够奋发图强,创造一个超越西方的真文明世界,但中国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依旧在销金帐中。新法螺先生为之大怒,将自己的肉体化为无数火球,欲将东半球之东半一举焚之,却不想误将灵魂掷下。这一掷,使得四分之一的灵魂带着肉体坠入地下,进入地底的另外一个中国,而另外的四分之三的灵魂则飘向宇宙于金星着陆,途中还看到了水星人的“造人术”。最终,四分之三的灵魂乘着宇宙气流回到地球,与从地底国出来的肉体成功结合。在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中,虽然可以看到以凡尔纳《月界旅行》及《地心历险记》为代表的太阳系漫游记与地底漫游记等类型小说的身影,但作为中国人书写的最早期的一部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故事相对完整,且表现出了一定的新奇意象,极大地引领了晚清科学小说的风潮。[45]还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颠覆了古典探奇搜秘的说部形式,并提供了一套新的雄浑(sublime)观念”[46]。“造人术”“催眠术”“脑电波”等书中涉及的这些“科学”元素,自然是该小说新奇意象的一些具体体现,而为了贴合“科学小说”的标签,书中除了频繁使用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相关的新名词之外,还对各种数值设置颇为细心,似乎同样也在展示这部小说的“科学”之处。例如新法螺先生坠落时,书中的描述如下:按第(一)秒一十四尺二二。第二秒四十二尺六六。第三秒七十一尺一。坠物渐加速率之公例。如炮弹之脱口。直往下落。[47]
所谓“公例”,即我们所熟知的自由落体运动公式:y=1/2gt2。通过此公式,我们可以轻易得知第二秒的位移距离是第一秒的三倍,第三秒的位移距离是第一秒的五倍。这皆与小说中的数值相吻合,所以徐念慈对照着公式一边计算一边行文的情形似乎并不难想象。[48]而另一方面,除了上述非常具体的数值设定之外,如前文内容梗概中所提及的风速每秒“数百万尺”那般,明显偏离科学常识的数值也非常多见。而如此倾向,同样出现在其他晚清科学小说之中。“百万”“百亿”这些极度夸张的数字,在营造奇幻氛围的同时,似乎也在表达着那个时代对待科学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无限向往。而“秒”这个时间概念,便为如此叙述以及想象,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具体且广阔的空间。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徐念慈对“时间”的兴趣之所在,并不体现于“未来”这个时间概念之上。实际上,“时间”作为构成《新法螺先生谭》的重要要素,迄今为止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那么,该小说中究竟暗含了哪些徐念慈对于“时间”的思考,以及他又是如何“把玩”时间本身的?我们需要把目光投掷于新法螺先生的地底“奇遇”。新法螺先生的肉体坠入地底国之后,与一位名为“黄种祖”的白发老翁相遇。但奇妙的是,这位老翁自称其出生只不过数十日。新法螺先生自然不信老人之言,打趣地说道三十岁的自己岂不是老翁之始祖?然而,老翁却向他解释道该国之人民,有出生数秒、数分钟就死的人,最长寿的也不过四个小时。随后,面对桌子上的“计时器”,新法螺先生与老人展开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具体如下:余即观桌上。果见有奇异之记时器。此器周约五尺许。有三针。针长八寸。但闻窣窣摆声。而三针无一稍动者。余曰:此器有秒针乎。翁曰。此长者秒针也。余曰。秒针胡不动。此针适已坏乎。翁曰。否否。秒针固非能一看即见其动者。余曰。何谓也。翁曰。君尚不知乎。是何年岁之大。而智识之幼稚也。余语君。一日当分为二十四时。每一时六十分。每一分六十秒。余曰。然。翁曰。每一秒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余曰。翁误矣。每一秒六十微耳。翁曰。否。余未闻有以六十微为一秒者。余之记时器。固以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为一秒也。[49]
“一千二百九十六万”无疑也是一个精心设定的数值,而与其他数值有所不同的是,徐念慈在此专门以夹批的形式,向读者仔细地说明了此处的时间换算问题。觉我曰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为时钟之二十一万六千秒。即三千六百分。即六十小时。即二日半。是黄种老人之记时器。以一秒时当今之二日半。一分时当今之一百五十日。一小时当今之二十五年。二十四小时当今之六百年。宜其最寿之人。不得过四小时矣。朝菌晦朔。蝼蛄春秋。世间物我之不齐。诚有如此哉。[50]
像徐念慈说明的那样,如果地底的一日与地上现实世界的六百年相当的话,那么轻而易举可以逆向推算出地底之一秒等于地上之“二日半”,即“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但细细思之,“二日半”这个数值的设定本身实在有些蹊跷,并且一日为什么一定要对应“六百年”这个时间呢?当然,把一切归为作者的个人喜好,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连坠落距离的数值设定都要参照物理公式的徐念慈,在需要夹批说明的地方却随意设置了一组数值,这种可能性让人难以信服。而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数字依旧是有来源根基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既不是“二日半”,也不是“六百年”,而是“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12960000这个数字,在西方被称为“柏拉图之数”(Plato’s number),是圣数之一。印度教中则有表示宇宙时间单位的“三分时”(tretā-yuga),即1296000年。二者虽然位数不同,但本质相通。而如此“三分时”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便促成了时间单位“元”的出现,“一元”即129600年。关于宇宙如何诞生,现如今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说,基本上依照的是北宋易学家邵康节(1011—1077)《皇极经世书》中的理论。而邵康节的宇宙论,不仅覆盖了现实世界,像是《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这些虚构的中国小说,实质上也处于他的宇宙模型之中。[51]邵康节认为,宇宙从诞生到消灭为一个循环,历时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称为“一元”。一元之中又分为十二“会”,一会(一万八百年)又分为三十“运”,一运(三百六十年)再分为十二“世”,一世即三十年。而如此“元·会·运·世”的时间体系,实则照搬自“年·月·日·辰”[52]。徐念慈采用“1296”这样一个象征着宇宙寿命,充满形式主义(maniérisme)韵味的数字,其对“时间”的设定不可谓不精心,其对“时间”的把玩之心,至此也终于跃然纸上。“1296”数字问题暂且搁置一边,这篇小说中所展示的地底国的“时间乐园”——流淌着不同时间的异界——同样可以看做是中国人循环时间观的产物之一。[53]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的相对性,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时间乐园”无疑是《晋书》以及《述异记》等记载的“烂柯”传说,即一个叫王质的人上山砍柴途中观看童子下棋,不觉间时光飞逝以至于斧柄已经腐烂的故事。王质回家后“无复时人”,故事就此终结,而像是《太平御览》等类书所收录的《东阳记》版本中,还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说明:“去家已数十年”。实际上,比起“烂柯”而言,更详细地阐述时间之相对性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四世纪成书的《神仙传》中,便有吕恭在仙界与仙人逗留两日,人间已过去两百年的故事。而除过仙界,地狱之中的时间流速似乎也与人间不同,最早的事例可以在唐代的《酉阳杂爼》中看到。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鹞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绐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窠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鹞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尔必为我暂留,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家,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诺,许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货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盖人间三日也。[54]
如此看来,新法螺先生于地底国的“时间旅行”,与其说借鉴了凡尔纳《地心历险记》之类的地球空洞说,倒不如说它根植于诉说时间相对性这一中国文学史上永恒不变的母题。而“秒”以及“微”所象征的更加精确化的西方时间制度,这一次只不过作为新的元素,被徐念慈带入到了这个母题之中罢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的是,徐念慈创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利用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桥段与母题来创作出一个诉说时间相对性的故事。与之相反,如何打破传统文学的束缚与窠臼,才是晚清时期诸多小说家之关心之所在,而徐念慈是否也一样?实际上,当我们仔细研读这篇小说中的时间设定,才会恍然发觉到,不管是地底国还是地上人间,这二者的时间流速其实并无差别。换言之,二者时间“密度”相同,不同的只不过是对时间的定义——时间单位罢了。假如我们在地底国,度过了地底国之“一日”的话,那么,我们对此“一日”的时间感知,实则有人间六百年之久,绝非人间的一日。所以在小说中,新法螺先生从地底国回到人间后,也并没有像“烂柯”中的王质一样来到几十、几百年之后的世界。明明身处于同样的“时间”之中,但对“时间”本身的定义与认知确有天壤之别,这难道不是当时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真实写照吗?而一秒的时间,可以再细分为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如此地底国的时间制度,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本应一致的时间在西方却能够被精细认知与计量这一现实的极度夸张。如此,我们或许便可以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阅读这篇小说,即徐念慈对地底国时间制度的设定与对“时间”的把玩,作为诉说时间相对性这一传统母题的戏仿(parody),向当时的中国人暗示了时间所蕴含的无限可能。结语如前文所述,“秒”最初在中国为长度单位,自唐以后,又转化成角度单位,主要用于天文学的计算。到了明末,经过传教士利玛窦的时间改革,“秒”才开始成为一个时间单位。但“秒”这一时间概念,初期仅存在于理论之中,直到拥有秒针的三针表被发明并于清朝中叶传入中国以后,“秒”才真正能够被用于时间计量。然而,三针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是作为高级饰品抑或是玩具才受到中国人的追捧。换言之,当时的中国人热爱三针表,绝非是为了追求更加精确的时间。所以,中国人关于“秒”的时间意识也就并没有因为三针表的流行而觉醒。但随着西方科学知识以及文化思想势不可挡地涌入晚清中国,“秒针”所象征的更加精确化的“时间”,便如同蒸汽机和“电气”一样,开始渐渐被中国人视为科学与文明的标志。而探讨“时间”主题,运用“时间”元素的科学小说,也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作为最初期完全由中国人创作的完整之作,便是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本文在末节通过关注该小说中的时间主题,具体分析了徐念慈如何“把玩”时间元素,以及揭示了晚清中国文人对于“秒”乃至“时间”本身新的认知与探索。How to Play With the Second Hand: Time Consciousness About“The Second” in Late Qing ChinaJin Bonan(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Human Sciences,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SAPPORO 001-0014)Abstract:At first, “the second”(秒) was a unit of length in China. It was not until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fter the time reform by Matteo Ricci’s, that “the second” began to become a unit of time. After the three-hand watch with the second hand entered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second” was really used as a measure of time.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regarded the three-hand watch as a high-end accessory. Therefore, the Chinese people’s time awareness about “the second” had not been awakened by the popularity of the three-hand watch. Later, as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ultural thoughts poured into late Qing China irresistibly, the precise time symbolized by the “second hand”, finally began to be gradually regarded by the Chinese as a symbol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which like the steam engine and electricity. Scientific novels that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who actively used the element of “time” also began to appear during this period. Among them, Xu Nianci(徐念慈)’s Xin Fa Luo Xian Sheng Tan(《新法螺先生谭》) was a pioneering work. In this novel, Xu Nianci completed the parody of the classic Chinese literary motif of telling time relativity through the setting and comparison of the time systems of the underground country and the real world, and showed the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the second” and even “time” itself.Keywords:The Second; Xin Fa Luo Xian Sheng Tan(《新法螺先生谭》); Late Qing Novel; China’s Time System; Consciousness of Time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22年第1期作者简介:金博男(1992—),男,陕西西安人,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中国人时间意识研究。
※日文原文「秒針の遊びかた——清末における「秒」の時間意識について」发表于《饕餮》(日本中国人文学会编)2020年第28号,由作者改订并翻译成中文。
[1]参见H. Bernard:《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下编,萧濬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0页。另参见张柏春:《明清时期欧洲机械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罗明坚应传教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之邀,1579年自意大利来到澳门,并于1580年12月第一次前往内地广州。
[2]参见李侑儒:《钟表、钟楼与标准时间:西式计时仪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1582—1949)》,政治大学史学丛书25,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11年版,第16—17页。李侑儒还认为,自鸣钟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因为自鸣钟最早进入日本的相关记录为1551年,而中国应当早于日本。
[3]参见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4]参见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21页。
[5]2019年,国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修改了描述,具体定义为:将铯-133原子不受扰动的基态超精细能级跃迁频率ΔνCs的值固定为9192631770赫兹,赫兹等于s―1。
[6]学界对于《孙子算经》的具体成书时间尚无定论。钱宝琮则在《孙子算经考》(《科学》1929年第2期)中认为成书于两晋(266—420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谈到此书可能出现于三国、晋或者刘宋,具体为公元280—473年。
[7]《孙子算经》卷上,郭书春校点,《算经十书》二,郭书春、刘钝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孙子算经》宋刻本等传本中,相关记载为“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但《隋书·律历志》的记载为“孙子算术云: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对此,郭书春如此考证道:“魏晋南北朝与两汉期间,度之单位为忽、秒、毫、厘、分、寸;自唐起,‘秒’改为‘丝’,宋刻本因此而改。”
[8]〔汉〕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41页。另〔汉〕刘德认为“秒,禾芒也。忽,蜘蛛网细者也”;颜师古针对“秒”字还有如此说明:“秒,音眇,其字从禾。”
[9]〔唐〕魏征:《隋书》卷十六志第十一律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88页。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二志第十二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1页。
[11]参见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的百刻计时制》,《科技史文集》第6辑天文学史专辑2,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12]〔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严一萍选辑:《百部丛书集成:原刻景印》集成之一四《稗海》,台北:艺文出版社1965年版。
[13]参见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4]参见Thorndike Lynn, Science and thought in the 15th centur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Natur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9, CHAPTER Ⅰ. 另参见Jacques Attali, Histoire du temps, Fayard, 1982, CHAPTER Ⅱ.
[15]由于太阳位置的变化,昼夜长短及日出日落的时刻每日都不相同,相关具体参数,该书亦有详细列表可供参照。
[16]表中数字均由左向右读。
[17][18]〔明〕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卷下,严一萍选辑:《百部丛书集成:原刻景印》集成之五十二《守山阁丛书》,台北:艺文出版社1968年版。
[19]参见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0]〔清〕崑冈续编:《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一《漏刻科》,清光绪12年敕撰光绪25年刻本影印,台北:启文出版社1963年版。
[21]本论中特指有时针、分针、秒针的钟表。
[22]David S.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17—418. “The earliest known spring-driven timepiece with a second hand—perhaps the earliest timepiece of any kind—is an unsigned Orpheus clock in the Fremersdorf collection. The date is estimated at between 1560 and 1570”。“俄耳甫斯”钟表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种常见钟表,钟表周身会镌刻俄耳甫斯的故事情节。
[23]参见Paul Pelliott, BULLETIN CRITIQUE(Reviewed Work: La montre “chinoise” by Alfred Chapuis), T’oung Pao(通報), 1920, Second Series, Vol. 20, No. 1: 66. 另参见Carlo M. Cipolla, Clock and Culture: 1300—1700, Walker, 1967: 86.
[24]〔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九《高宗诗文十全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2179—218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5]张柏春:《明清时期欧洲机械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26]〔清〕徐朝后:《自鸣钟表图说》之《钟表名目》,徐朝后:《高厚蒙求》三集目,同文馆,1887年刻本。
[27]参见李侑儒:《钟表、钟楼与标准时间:西式计时仪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1582—1949)》,“政治大学史学丛书”25,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11年版,第75页。
[28][29]〔清〕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张智主编:《风土志丛刊》27,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二分明月”为扬州别称。
[30]〔清〕杨米人:《都门竹枝词》,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后汉书·梁统列传》中记载梁翼爱好“臂鹰走狗”,后世用“臂鹰”借指狩猎或者外出游玩。“手裹牛皮”或指皮手套。
[31]Carlo M. Cipolla, Clock and Culture: 1300—1700, Walker, 1967: 88. “While the Europeans were using lenses to produce microscopes, telescopes and spectacles, the Chinese delighted in using them as charming toys. They did the same with clocks. Lenses, clocks, and other instruments had been developed in Europe to satisfy specific needs felt by European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contrivances fell unexpectedly out of the blue and quite naturally the Chinese regarded them merely as amusing oddities”.
[32][33]〔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43页。本书为湖南省图书馆所藏郭嵩焘日记手稿经整理而成,原日记并无题,现题目为编者钟叔河等所加。
[34]〔清〕徐建寅:《欧游杂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76页。
[35][36][37]〔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26、326、620页。
[38]参见〔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章。
[39]〔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74页。
[40]参见金博男:「「猫時計」研究——中国人は猫の瞳に時刻を読んだか」,『饕餮』2018年第26号,日本中国人文学会編,第2—19頁。
[41]参见金博男:「清末における「日曜日」の受容」,『時間学研究』2019年第10号,日本時間学会編,第39—57頁。
[42]参见武田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館』(上),東京:大修館書店2001年版,第二章。
[43]参见金博男:《“壬寅”轮回——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时间观念》,《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
[44]这两部译作均刊载于岩谷小波的童话集《世界お伽噺》(1899—1908)之中。日译本原题中的“法螺先生”即閔希豪森男爵,日语中“法螺吹き”即吹法螺,说大话之意。另“独逸の部”意为“德国卷”。
[45]参见武田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館』(上),東京:大修館書店2001年版,第二章。
[46]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CHAPTER Ⅴ, 258. 中文翻译引自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47]〔清〕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上海:小说林社1905年版,第11页。括号内容为笔者补正。
[48]最早由传教士艾约瑟口述,李善兰翻译的力学著作《重学》(1859)之中,关于重力的数值为“二十七尺六寸”,而由徐念慈所给出的数字逆向推算,得到的重力值为“二十八尺四寸四分”。二者之间略有出入,所以徐念慈当初具体参考了什么书目进行计算,目前还不得而知。
[49][50]〔清〕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上海:小说林社1905年版,第14—15页。“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出自《庄子·逍遥游》篇,“蟪蛄”为蝉之一种。而该书中所记为“蝼蛄”,为蟋蟀之一种,疑是笔误。
[51]参见武田雅哉:『桃源郷の機械学』,東京:作品社1995年版,第14頁。
[52]参见〔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六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3]参见中野美代子:『ひょうたん漫遊録 記憶の中の地誌』,東京:朝日新闻社1991年版,第一章「楽園と地獄」;另参见中野美代子:『仙界とポルノグラフィー』,東京:青土社1989年版,「仙界とポルノグラフィー」。
[54]〔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爼校笺》续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83页。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