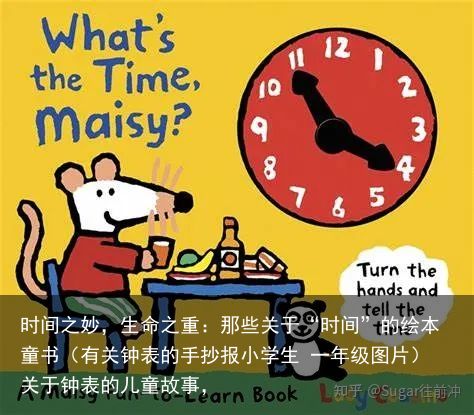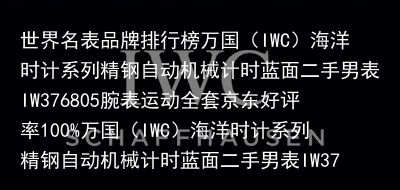钟表漫记(上)(关于钟表的数学题)关于钟表的儿童故事,
钟表漫记(上)
□吴金高
世间所有事情,影响决定其起始、进程、快慢与成败的指标要素,最硬性的有仨:时间、地点、人物,所谓天时、地利与人和。要是按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好像时间还不算最关键,但毕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嘛。因此,自古以来,人们计算做事行动的起时、用时、占时、耗时、终时,往往得提前选定、准确掐算、及时累计。
随着人们对准确计时工具的迫切需求和日益探寻,钟表便应运而生。
01
千百年来,上至真龙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都很看重施行布事的时辰、时更。古人计时的水漏、沙漏,还有日晷,都是“广义钟表”发明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钟表诞生之前,描摹人们生产劳作、生活起居间隔的时与刻,多借助日月升降、更夫敲击和雄鸡啼鸣这些“显活”的物象,喏——“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日月轮回,天地晨昏,戊亥子丑,月牙五更……这些时间的标记,现实中无事无处不在,与古诗词一样,大众文艺作品中也留下不少与“时间”有关的妙语、轶闻:电影《闪闪的红星》里,主题歌《映山红》所唱的“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是子夜时分普遍心理的真情诉说,更是期盼红军快回的殷切念想,一语双关,赋予了实际时间以革命的象征意义。特别经典的“半夜鸡叫”,随着小说《高玉宝》的出版,加上小学教科书的节选,以及同名动画片的放映,几个忍无可忍的长工将计就计痛打贪心财主的故事广为流传,而故事的缘起,就是那个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多干,半夜学鸡叫,硬生生把鸡圈里的那群“活钟”提早激活、“拨快”了好几个钟头。
我父母他们那辈人,头脑中大多没有钟表所界定的二十四小时,但也自有他们约定俗成的时间说法:
“明早什么时候去铜城赶集啊?”——“五更头吧,早些个走占个好摊子。”
“你家小五子什么时候落地的?”——“鸡叫头遍哎。”
“小大子上书房走多早哇,天才麻花亮哩。”
“太阳都中过西了,怎么还没吃中饭?”
“快起来啊,太阳都过树梢子了!”
“明个上他老舅舅家吃暖房酒,早点去,不要等天打黑影子才走。”
……
02
有刻度、计实时的真正的“钟表”,发明并发展于15、16世纪。
如今,在功能强大、广为普及的手机面前,钟,表,在计时上似乎已显得“过时”,回望其更替兴衰的历程,有明显的起落,好像就是近几十年的事。
在我国,钟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稀罕物,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钟表还很稀缺,那“三转一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连城里人都梦寐以求,在我们乡下,更是极为少见。
我小时候见过的手表,有印象的,就不是哪个人戴的,而是在电影上。
老电影《董存瑞》中,总攻即将开始,赵连长说,3:30全团要发起总攻占领隆化中学,现在离大部队总攻还有25分钟。中学周围的几个火力点被我突击队员一个个炸掉,赵连长抬腕一看手表,表针已到3:25位置,画外音是他的“离总攻发起的时间还有5分钟!”随着爆破手应声而起,最顽固的一个大碉堡也被炸翻,战士们迅即潮水般往前冲锋……谁知,横跨旱河的那座桥上突然喷出几条火舌,眼见战士们一排排倒下……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在火力掩护下,冲到了桥下,可怎么摆弄,炸药包就是顶不上桥体……这时,赵连长再次看表:分针即将覆盖“6”,秒针也快接近“12”……在他万分焦急的一句“哎呀,来不及啦!”之后,就是英雄舍身炸碉堡那感天动地的壮举。
是啊,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国内百姓别说戴手表,见过、甚至听过的都极少极少。即使是军人,革命队伍里的,也只有一定级别的首长、指挥员才能戴得上手表。据说,当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戴的手表,还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临时赠送的呢。
的确,那时候,钟表是比枪支弹药还重要、还金贵的!
我记忆中,电影中凡出现钟表镜头,基本都是紧要、危急时刻。
印象很深的,是抗美援朝的老片子《铁道卫士》,接近尾声时,在飞奔的军列顶上,一边是我公安高科长被敌特马小飞掐昏过去,一边是悬挂在火车扶手上晃荡不已、嚓嚓作响、随时都能爆炸的一枚定时炸弹。千钧一发之际,高科长苏醒过来,拼尽全力够到手雷并沉着镇定地拧掉定时按钮,终于排除险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几十年过去了,电影情节已经模糊,但那枚与时钟绑在一块的有经纬刻痕的椭圆手雷,连同那一串扣人心弦的钟秒嚓嚓声,一直印象深刻。你看,钟表本来是计时的,当它的定时闹铃机关和炸弹引信安连在一起,就成了特别致命的武器。
外国故事片中,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情与钟表密切相关。游击队员在街上接头,所用的暗号,不是什么口令,也不是什么纸条,而是各自出示的同款手表。他们经常联络的固定地点,是一个钟表店,里面陈设华丽,墙上、台桌上,各式挂钟、座钟琳琅满目。店主,那个慈祥而沉稳的老钟表匠,是片中一个很重要的配角,其真实身份是游击队员,还是骨干分子,负责联络站工作。不离其身的,还有一个与他的“掩护性职业”特别相称的道具——怀表,走在街上,表链子晶亮耀眼,在西装衣扣处若隐若现。老钟表匠以钟表店作掩护,也经常按照这块怀表的指示,为了萨拉热窝,配合瓦尔特,与德军机智周旋……钟表,成了贯穿这部影片始终的或明或暗的主线,仔细回味,几次响起的主题音乐旋律当中,就有某种乐器模仿着的钟声,深沉、雄壮、激越。
现在网上回放《董存瑞》,快进,暂停,能清楚地看到赵连长戴的那款手表:表盘正中上方,是ROAMER几个字母,百度一搜,是瑞士的“罗马”表呢;那手表上似乎还有划痕斑点,抑或是老电影本身的黑白灰蒙,但还是感觉表盘清晰、刻度精致、时分秒三针修长,秒针末端还是个三角的,特别生动;尤其整点位置的设计很考究:6个单数点(1、3、5、7、9、11)位置是水滴状,6个双数点位置除了数字外,还有个圆点,所有“水滴”和圆点,都和时针分针上的内嵌一样的色调,那种荧光材料独有的淡绿色(实际的)——这是夜光表的特征,战争岁月多么需要这样的手表啊。历史悠久,国际名牌,“罗马”表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牌子,以前的确很响,但人们毕竟是听说的多,购买、使用的少,就一直想当然地以为,罗马表是罗马尼亚产的。七八十年代常听的一段相声里,就抖了这样一个“包袱”:有人问一新婚小伙子,怎么买了罗马手表?他说,戴罗马表有意义啊,罗马尼亚早就同咱们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最近总统又来访问,戴上它,不也表示表示嘛。
受电影的影响,我们小孩子对手表也经常心驰神念,那时候,差不多每个小学生都在自己的手臂上画过手表。手表的大概样子个个知道,一般都是先画圆圆的表圈,然后时点刻度,最后中心、三针。表带当然不能缺少,自己的右手在左臂上画,转过臂膀,画得宽窄合适、线条衔接得妥帖无痕,那真是本事。也知道用铅笔画,太淡,几乎看不见;钢笔画,容易掉色,还会脏了衣服;最理想的,是蓝色圆珠笔,经久耐看,连磨带洗,“戴”上个两三天也没问题。几个侄儿很小的时候我都带过、哄过,让他们不哭不闹,逗他们开心,很常用、很管用的招数,是在他们的小膀子上画个手表。
03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周边人家,大多和我们一样,是没有钟表的,男女老少,居家出门,几乎都没有任何“看”时间的依靠,可是,大家做家务、干农活,或是上书房、出远门,作息如常,起居有恒,往返不误,想想,占的是广播的便利。
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地方,广播就是钟表。
那时候,我们农村里,家家户户最显眼、仅次于电灯的很重要、最常用的“电器”,就是广播喇叭。那种绕线圈带磁铁的舌簧式喇叭最为常见,讲究点的,会蒙上布,外罩个木盒,给人一种“音箱”的感觉,听起来似乎更雄浑悦耳些。它们大多被固定在堂屋左(右)侧山墙上,或户外的走廊里,墙体或木柱上钉个铁钉,挂上去就行。喇叭上有两根引线,一根外接进线,一根是地线,续长后接入下方泥土即可。过去农家室内地面大多就是干土,极少数的可能铺砖,好在插一根铁丝入地,都不成问题。
每天早中晚,县广播站各有一次播音。早上,5:50开始,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那是比任何整点节目更受关注的金牌节目、红色声音,这开始的时间多少年如一日没有变化;7:30天气报告后,第一次播音结束,也顺告下次播音开始时间。中午,11:25第二次播音开始,12:00 “对农村广播”,当《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乐曲响起,那基本就是学生放学路上、社员收工回家、屋顶炊烟袅袅、家家准备午饭的时候。晚上,大概6:00吧,第三次播音开始,到了8:00,转播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是一天中另一个重磅热播节目,相当于现在的电视《新闻联播》。在农村,这档节目播出时,夏天里,人们大多还在田间场头忙碌;到了冬天,则是掌灯时分,多半已吃过晚饭。
听着广播里是什么节目,就知道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除了故意的拖延,好像就没有什么人耽误过什么事的。
广播响、广播停,是一天当中很具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我们上小学、初中时,早上、中午啥时上学校,一般都是“广播停”的时候动身走,肯定不会迟到。晚上,“联播节目”之后,广播喇叭里耳熟能详的结束曲《国际歌》响起,在冬天,差不多就像军营里吹响了熄灯号,不少人家基本已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光景,过一会儿,周边远近就万籁俱寂了。人睡下,好像才一觉醒,远近的公鸡叫了,头遍、两遍,睡梦里听的心里揪揪的,过一会儿广播一响,又得起床了啊。
每天早上、晚上,还有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要帮助做些家务的,早中晚,那特别特别熟悉的开始曲《东方红》(交响合唱,后来逐渐改成《歌唱祖国》)一响,就是我们开圈喂鸡、淘米洗菜、烧火做饭的统一号令,也基本是大人出门上早工、午歇吃中饭和下晚工回家的权威批准。
以前,县广播站院内,竖着个城区乃至全县都独一无二的高杆子,从下向上,由粗到细的几截黑色的木杆依次绑接着,高高的,站在下面朝上望,还有点摇晃呢,最顶上,安了个平铺着的“非”字形金属玩意,听人说那就是接收天线,中央台、省台的广播信号,包括那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都是从那里接收、再转到全县家家户户的广播里的。县广播站将上级规定节目,加上自办节目,按照固定的时间安排,将信号逐级传输下去,到公社有放大站,经各大队部的转接,再依次传到所属生产队的一家一户,那信号的“终端”,就是一个个广播喇叭,把它们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一根电线。我所知道的 “县——社——队三级广播网(有线)”,当时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
那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电线也是如此。公社放大站到各大队的广播线,就那么一根,而且还与大队部那个手摇电话机共用一线。公社有要事来电话,一般只能在广播停以后,放大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广播上先喊上一句:“请**大队把广播线的闸刀拉下来,马上要打电话了。”于是,广播线就迅速切换成了电话线。电线杆也是因陋就简,有的借用农用电杆,有的依靠房屋的外墙或廊柱,有的干脆搭在枯树上,即使单独的,也不过就是一根树棍或毛篙。
但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农村里,哪怕是远离大庄台的单门独户,家里广播照响。要是广播或线路出了问题,在当时可是大事,好比今天,停水了,断电了,手机没信号了,那还了得,不过不要紧,各大队有专配的线路维护员呢,总是随叫随到。
这些,与钟表有关系吗?当然有,上上下下对广播的重视和普及,不等于就是维持我们赖以报时的 “特殊钟表”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不竭动能吗?
人们对广播的依赖,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早上起身,放牛或者拾粪,也钓鱼,然后回家吃早饭去上学,几乎从来没耽搁、迟到过,想想,靠的就是广播:不但在家有广播,出门在外,电线杆上,生产队公房的屋脊上,大队部前的树梢上,还有附近华水农场前前后后几幢房屋的顶上,好多处都安有广播,还是那种“颈细、嘴大、舌头圆”的高音喇叭。四面八方的广播喇叭正常播音时,整点会报时,而那一个个固定的节目,从开始提示、语词特点到播音风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大家早已听惯了,早已是很清楚、很及时、很精准的时间提示了,大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总之,在室外,广播声绝对如影随形,根本不会误你什么事。至于广播停的时候,农民在田里,工人在车间,学生在课堂,时间就有各自的集体以另外的方式稳妥把控着,同样不会误事。
我经常回想,那时家里的广播,好像也没有开关,更没有音量控制,声音那么响,几乎没怎么关过,却也没人“嫌吵”啊,感觉就没有一点干扰,什么原因呢?现在想想,也不奇怪,大人小孩,几乎都是成日带夜的忙,谁不累、不困啊,倒下就睡,谁还在意广播声呢。再说,里面传出的,可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都是要听、要学,有的甚至是要背的呢。偶尔,哪家有小孩哭闹不止,或是家里来人说要紧的事,想临时“关”下广播,很简单,只要不是黄金时段,没播紧要通知,地线一拔,马上就清净了。当然,一会儿还得插上地线,恢复广播,不然,等于是钟表停摆,会误事的。倒是有时嫌它声音小,一看,地线旁边的泥土干裂了,松动了。插地不实,等于接触不良啊,解决的办法,我们小孩子都知道,往下深插一些,再倒上点水,踩实几脚,音量马上就有改观。
全国亿万民众充分感受广播便利,及时感知最大突发事件的,是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天。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防震棚里上课,旁边林庄东头的高音喇叭突然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接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男播音员异常低沉凝重的预告,似有黑云压城。大家再也无心上课,疑惑而忐忑地等了近一个小时,再次听到报时后,广播里就播放出建国以后反复播报次数最多、播报时间最长、内容最惊天动地的《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还有平时极少听见的哀乐。
过去,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人特别崇拜广播,没人特别感谢广播,但广播,到时就响,不用操心,风雨无碍,而且,不用缴费,无需携带,也不怕丢失,是准确报时、及时传播大事的天籁之声,方便至极,也神圣之至。我们真的应该为它唱上赞歌的。
的确,如今钟表、电视、手机的许多功能,先前的广播早已集于一身。虽然电视,连同钟表、手机早已不算稀奇,但广播永远是老大,不然后来怎么是叫“广播电影电视部”、“广播电视总台”的呢?
(待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生于江苏金湖县黎城公社上湾大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